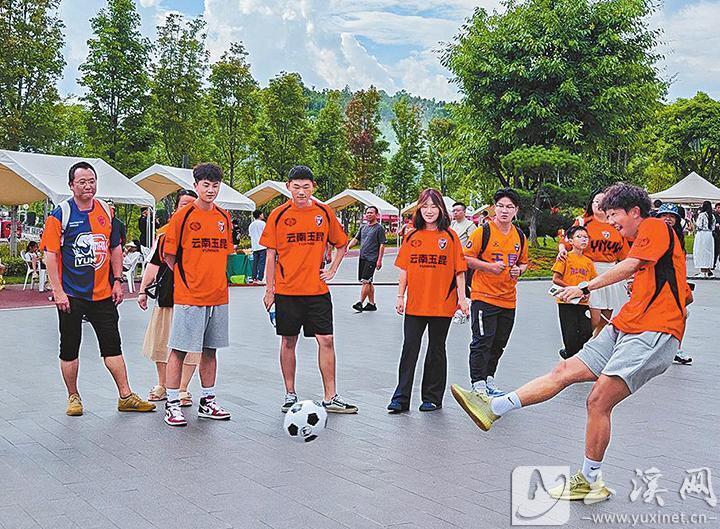什么是乌龙茶?哪的最好喝?一次讲清楚
神农尝百草那天,怕不是故意的。
几片叶子落进滚水里,苦中带点回甘,竟比草药顺口。
这一尝,就把茶尝成了中国人的命根子。
唐朝人喝起茶来像吵架,茶饼得碾得粉碎,煮时还得抡着胳膊搅,跟拌水泥似的。
陆羽写《茶经》那会儿,怕也是看烦了这乱象,才正经八百给茶立规矩。
到了宋朝,文人把茶点得跟画画似的,一勺水下去,白沫能转出山水来,
比现在的咖啡拉花讲究多了。
茶馆是个妙地方。
北京的大碗茶摊,成都的盖碗茶桌,三教九流凑一块儿,茶没喝几口,街坊的官司、城里的新鲜事全听遍了。
苏轼说 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,其实茶比佳人实在,穷人喝得起,富人也稀罕。
茶马古道上的马帮,背的哪是茶,是山里人与外界的念想。
如今超市里的袋泡茶,跟古代的团茶差着十万八千里,
可倒进杯子里,那点苦后回甘的意思,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。
茶这东西,不挑人,你急,它慢慢泡;
你闲,它陪你耗,比谁都懂过日子的道理。
乌龙茶这东西,原是武夷山的意外。
康熙时王草堂记着,茶农晒青摇青,叶片半红半青时炒焙,就有了这味。
传说清兵过境,茶青被压得发软泛红,炒出来倒有了醇厚气,
跟过日子似的,歪打正着常有。
老技师守着“双炒双揉”,铁锅翻涌间,茶叶滚出了筋骨。
“岩骨花香”不是吹的,是烟火气熏进岩壁,又渗进茶汤里的。
文人爱它“绿叶红边”,元稹“夜后邀陪明月”,苏轼“且将新火试新茶”,都借茶说人生的拧巴。
潮汕人喝工夫茶,小杯慢斟,茶汤在舌尖打转,倒像把日子泡进了陶罐。

台湾新竹的茶山云雾里,藏着个娇滴滴的“东方美人”。
这茶原名膨风茶,说来有趣——早年茶农被虫咬了茶树,心疼得直叹气,
哪知做出的茶竟飘出蜜香,卖了个天价。
乡亲们笑他“膨风”(吹牛),谁知这“吹牛茶”真成了贡品,连英国女王都夸是“东方美人”。
这茶娇贵得很,非得让小绿叶蝉叮出满身红点不可。
虫儿一咬,茶树便分泌出蜜汁,再经六成以上的发酵,白毫乌龙便裹着果香、蜜香、花香三层味,泡在杯里跟美人跳舞似的。
端午过后是采茶季,茶姑们背着竹篓上山,专挑被虫咬过的“一心两叶”。
这茶上市要等秋凉,头茬的尤为金贵,一斤能换十二包白米。
如今虽不用再靠它换米,但老茶客们仍惦记着这口“虫咬的甜”。
产自广东梅州大埔县,千年种茶史,明清时便跻身梅州八大茗茶。
西岩山云雾缭绕,茶树吸足天地灵气,条索肥壮紧结,色泽乌褐油润,
冲泡后花蜜香扑鼻,汤色橙黄明亮,入口醇厚甘润,
回甘透心甜,老茶客一喝就懂“透心甜”是啥滋味。
制作讲究晒青、摇青六道工序,摇青时“绿叶红镶边”最是绝活,足火烘干锁住沉香。
春茶品质最佳,秋茶亦带果香,四季皆有供应。
客家人讲“茶米”当日常,大埔乌龙就是茶桌上的“硬通货”,
外地人来必带两包,本地人日日喝不腻。

广西龙州县的“茶中仙子”,2016年拿下国家地理标志保护,是龙州人捧在手心的宝贝。
老茶农说,这茶树是清朝末年从深山“请”下来的,原本野生野长,
后来嫁接了福建铁观音、台湾金萱的苗,才成了现在的“混血美人”。
做青时摇青机一转,叶边泛红如胭脂,香气直往人鼻子里钻,当地人管这叫“茶在跳舞”。
喝一口,兰花香裹着蜜甜在舌尖打滚,汤色金黄透亮像山涧落日。
春茶四月最鲜,秋茶九月更醇,龙州人端着搪瓷缸泡一天,
见面就喊“呗侬,得闲来嘢茶!”
这茶喝的不是水,是龙州的云、雨和百年光阴。
产自广东大埔西岩山,这儿的茶树喝着云雾长大,芽叶肥得能掐出水。
唐代西竺寺的僧人就在山顶种茶,
清嘉庆年间扩种到万株,年产千斤供香火,喝过的乡绅都说“这茶,香到心肝头”。
70年代改进工艺后,更成了地理标志产品,拿过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。
茶汤泡出来橙黄透亮,喝一口,醇厚得像山涧水滑过喉咙,回甘里带着花蜜香。
老茶客说“西岩茶,香、甘、清、滑、醇,五样全占”,冲十几泡还带味,叶底红镶边像朵花。
本地人管喝茶叫“食茶”,逢年过节必泡一壶,连不喝茶的娃闻了都喊“好食”。
春茶4月采,5月就上市,新鲜得能尝到露水味。
闽南乌龙里的“佛手香”,产自福建永春县,历史可追溯到北宋。
话说当年安溪骑虎岩寺的和尚,把茶树枝嫁接在佛手柑上,
硬是让茶叶泡出了佛手柑的香气,
后来传到永春狮峰岩寺,茶农们一传十、十传百,种得满山满谷都是。
这茶树叶子大得像佛手,绿芽红芽都有,春天4月冒头,夏天再摘两茬,秋冬天还能收一拨。
这茶好喝在哪?
干茶卷得像海蛎干,乌润油亮,泡开之后汤色金黄金黄的,香气像佛手柑混着雪梨香,甜丝丝的。
喝第一口有点涩,但马上回甘,像吃了颗蜜饯,喉咙里都甜津津的。
老茶客说这是“佛手韵”,耐泡得很,五六泡还有味。
永春人讲究“春水秋香”,春茶最鲜,秋茶最香。
现在头茬春茶刚上市,茶农们凌晨四点就上山采,露水还没干就摘下来,晒青、摇青、杀青,每一步都马虎不得。

台湾鹿谷乡的“茶中圣品”,那叫一个“得劲”!
清咸丰年间,林凤池从福建武夷山背回36株青心乌龙茶苗,
种在冻顶山上,这才有了这口鲜爽。
您猜这山为啥叫“冻顶”?
早年茶农上山,脚尖得绷得溜直,生怕滑下去,
闽南语里“冻脚尖”就成了地名,山顶叫冻顶,山脚叫冻脚,够有意思吧?
这茶啊,半发酵,热团揉的工艺,揉成半球状,墨绿带金边,
冲泡开汤色金黄透亮,香气清雅得像桂花混着焦糖,
喝一口,醇厚回甘,喉韵悠长,花果香在嘴里炸开,桂圆、红枣、蜜桃味儿,
回甘还带着焙火香,后劲足!
每年4到5月,春茶上市,茶农们忙活得脚不沾地,就为这口鲜。
冻顶茶在台湾茶界地位高,有句俗语“北包种,南冻顶”,您品,这地位!

清咸丰年间,宋帝赵昺南逃时喝过这口茶,直夸“得劲”,赐名“宋茶”,后人叫它“宋种”。
这茶啊,半发酵,炭火烘焙的功夫深。
初焙、复焙、足火,三道火候下来,香气跟开了挂似的。
冲泡开汤色橙黄透亮,花香混着蜜香直往鼻子里钻,喝一口,醇厚回甘,
喉韵像被山泉洗过般清爽,
后劲还带着焙火香,老茶客都爱这口“山韵”!
正宗单枞得经三次炭焙,青味褪尽,香得纯粹,喝一口,仿佛看见茶农“冻脚尖”上山,
汗水滴进茶园里,
这茶,喝的就是个实在,喝的就是个历史!

安溪虎邱镇罗岩村的茶农魏珍,咸丰年间探亲归途,
在北溪天边岭的石缝里扒拉出两株开得扎眼的野茶树。
这树怪得很,清明刚过就冒芽,叶子黄绿透亮,炒出来的茶汤金晃晃的,香得能飘出三条街。
老辈人讲,这茶是王淡姑娘从西坪珠洋村带回来的"带青"礼物,
闽南话里"王"和"黄"、"淡"和"棪"谐音,慢慢就叫成了"黄棪茶"。
这茶啊,条索卷得跟金丝似的,泡开之后水蜜桃香混着桂花味直往鼻子里钻。
老茶客说它"未喝先闻透天香",嘬一口,甘甜得舌底直冒津水。
虎邱人讲"好呷"时,总要配上这茶,
说是比铁观音早二十天上新,四月中旬就能喝上头茬鲜。

乌龙茶里的“扛把子”,产自福建武夷山那片“石头缝里长仙草”的地界。
老辈人说,唐代文人拿它当宝贝送人。
乾隆爷喝了都夸“气味清和兼骨鲠”,
您品,这“骨鲠”俩字,活脱脱就是岩茶的魂儿,喝一口像咬了块硬骨头,回甘却甜得人舌尖打颤。
这茶做起来费事,得经过晒青、摇青、炒青、焙火十几道工序。
焙火最见功夫,轻火茶像小年轻,香气清得能飘出三里地;
足火茶像老江湖,滋味厚得能挂住舌头。
您要是七月来,能赶上轻火茶尝鲜,茶汤金黄透亮,喝一口“真恰”(闽北话:真好)!
等到了十一月,足火茶才慢悠悠上市,
那茶汤橙红透亮,咂摸一口,够力(闽北话:够味)!
这茶啊,喝的就是个“岩骨花香”,跟咱老百姓过日子似的,先苦后甜,越品越有味道。

这茶中君子,打清雍正年间就在这儿扎根了。
西坪镇的山坳坳里,老茶农魏荫做个梦,观音娘娘指了棵茶树,他起来一寻,嘿,还真有!
后来王士让这酸秀才,把茶献给乾隆爷,皇帝一喝,眼睛都亮了,
说这茶“乌润如铁,韵似观音”,当场赐名“铁观音”。
这茶条儿卷得像蜻蜓头,冲泡开汤色金黄,兰花香直往鼻子里钻。
秋茶上市在九十月,春茶五月也有,但秋茶更醇厚。
安溪人说话有趣,“食茶”不说喝,“这泡茶真够力”就是夸好喝。
铁观音分清香、浓香、陈香三种。
清香型像小鲜肉,清汤绿水,适合夏天解暑;
浓香型是老江湖,炭火焙过,暖胃又回甘;
陈香型是老古董,越存越香,跟普洱有一拼。
安溪的山雾水,配上老茶人的手艺,这茶喝一口,七泡还有余香,不信你试试?
你看那茶馆里,茶博士拎着铜壶满场转,茶客们端着杯子眯眼笑。
“甭管多大事儿,”老张头吹开浮沫啜一口,“先喝透了这杯茶。”
隔壁桌吵架的两位,第三泡茶还没出汤呢,倒先勾着肩膀笑作一团。
日子就在茶沫里浮浮沉沉,
您要愁得烫嘴,搁杯里晾晾;闷得发苦,续道热水。
茶叶终归要沉底的,可那点回甘味儿,早顺着喉咙溜进心肠了。